- 搜索
東莞長安電子廠千余留守工人 索要補償金要求被解雇
因工廠停產,東莞長安霄邊平謙電子廠的100余名“留守工人”,從4月1日到8月6日度過了他們史上“最輕松也最無聊”的4個多月。這段時間里,車間機器封存,工人每天閑呆在廠里,聊天、打牌,無所事事,只能領到基本工資。僵持了4個月后,廠方突然張貼停工放假通知。工人們擔心該廠人力資源部負責人鄒某離開而使他們的補償金泡湯,遂將鄒困在廠里,要求被解雇。最終引發鄒某提刀“闖關”,無奈被“人墻”攔住……
一邊是工人閑在工廠聊天打牌度日,一邊是工廠中層管理人員提刀“闖關”。這樣的“劇情”充斥著濃濃的酸楚味。顯然,平謙電子廠工人們的遭遇,并非個案,而是中國外向經濟低迷之下勞資關系的一個縮影。事實上,類似的案例并不鮮見。比如一個月前,東莞大嶺山的圣馬來工藝品廠也發生工人集體要求“炒魷魚”。
這種經濟低迷下的“僵尸工廠”現象,無論于廠方還是勞動者來說,都盡顯無奈之感。客觀而論,一般情況下廠方并非故意不開工,而是應對經濟低迷的無奈之舉。應看到,在經濟低迷之下,對于那些訂單利潤很低乃至負利潤的企業來說,訂單越多,開工越足,也就意味著企業損失越大,而這在某種意義上無異于自殺。于是,選擇長期不倒閉、不開工、放長假、只發最低工資,也就成了企業的“理性”選擇。顯然,企業的這種選擇,目的一般有二:一是借此“逼走”員工從而規避巨額補償金;二是企業甩掉包袱,以求茍延殘喘。
盡管“僵尸工廠”的背后有著企業的無奈,但相對于那些“被放長假”的工人們來說,企業依然強勢。企業的“僵尸”行為,并未違法,比如《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》第三十五條就明確規定:“用人單位沒有安排勞動者工作的,應當按照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80%支付勞動者生活費,生活費發放至企業復工、復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。”然而問題是,對于那些本就工資微薄的工人來說,企業長期發放的那些可憐的基本工資,顯然不敷生計,只能被迫放棄各種補償自行走人。
經濟不景氣下,企業還可以在法律法規的“庇佑”下,通過“拖字訣”、“僵尸工廠”行為,將企業風險轉嫁到勞動者身上而順利脫身。而于勞動者來說,卻別無選擇,只能接受“想再去找個好廠上班,但廠方一直耗著不辭退我們”的兩難處境。在中國的勞資關系中,勞動者本已處于弱者地位,而今企業的“僵尸”行為,無疑令其雪上加霜。
經濟危機下的“僵尸工廠”現象,一方面說明了企業轉型之迫切,另一方面則暴露了法律的空白。從經濟理性人和法治的角度來說,企業的“僵尸”行為,似無可指摘。然而從社會道義上講,企業轉型升級、應對經濟危機的代價,顯然不應由弱者來承當;而法律的空白,更不應獨讓勞動者來填塞。相反,作為弱勢者的企業工人的權利,更應有堅實的法律來作保障。而這,有賴于地方職能部門的積極作為。
- 上一篇:膜法海水淡化技術的應用與進展
- 下一篇:英特爾:收購富士通半導體無線產品公司
相關閱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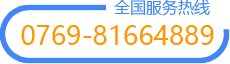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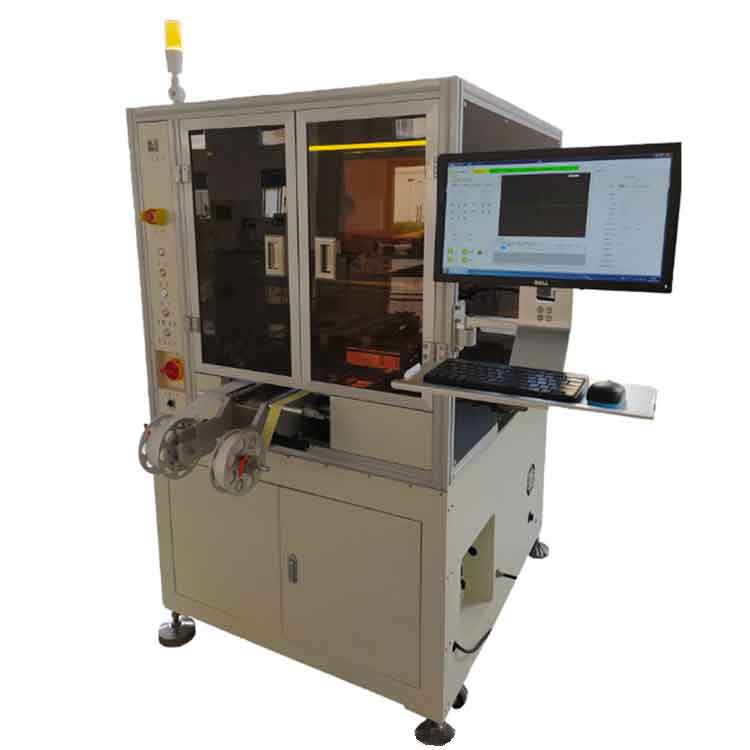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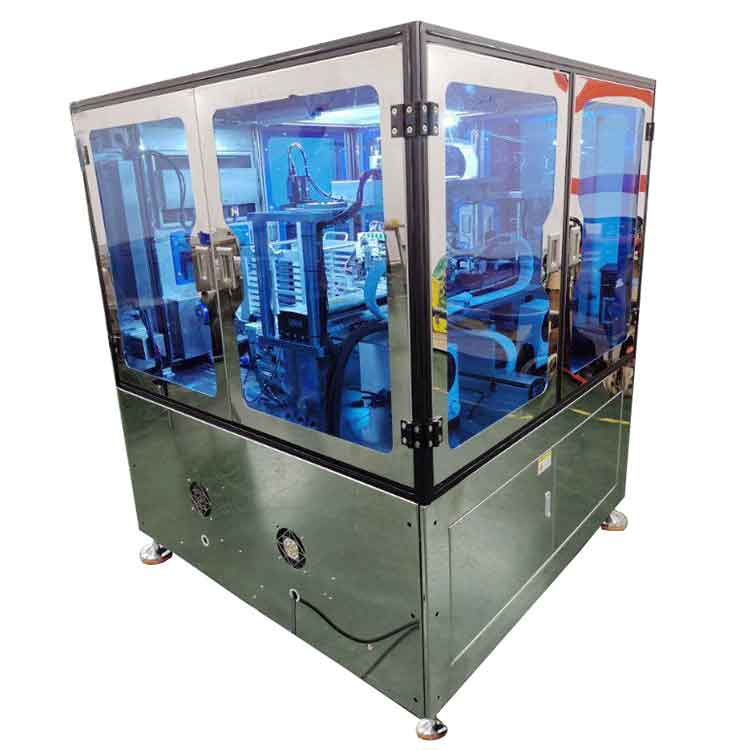


 掃碼添加微信
掃碼添加微信